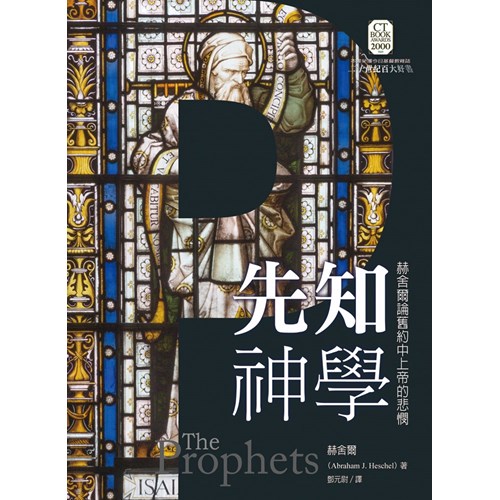
《先知神學:赫舍爾論舊約中上帝的悲憫》
作者:赫舍爾譯者:鄧元尉、邱其玉、徐成德、應仁祥
書系:里程碑
頁數:736頁
定價:950元
79折特價:751元

 線上試讀
線上試讀
2020年8月31日截止

「先知是什麼樣的人?」這是我父親在《先知神學──赫舍爾論舊約中上帝的悲憫》(The Prophets)一書開頭的提問。先知是一個痛苦的人,在「他所說即將發生的景況下,他的生命與靈魂都置身危急關頭」,因此之故,先知也是一個能夠聽見痛苦者「無聲嘆息」的人。在一般想像裡,我們把先知想成一個能夠預先說出未來的人,警告人要為罪接受神聖的審判,也要求整個社會秉持公義。然而,如此的看法卻無法明白「上帝在先知的話語裡震怒不已」是什麼意思?我們也許都批評過社會上的不公不義,卻勉強還能忍受,可是對先知來說,「即使只是一件微小的不義,也在宇宙裡占有一定的分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憤慨?先知的反應會不會太超過了?
然而,先知這樣的悲憫,才正是關鍵所在。在我父親看來,先知預言最重要的地方,不在於當中的信息,而在於先知作為見證人的角色,他讓上帝被人看見,不只是揭露上帝的旨意,也揭露上帝內在的生命。成為一位先知,我父親寫道,就是要與上帝的情感相伴,體驗與神聖意識的共融。先知聆聽上帝的聲音,從上帝的眼光來看這世界。
的確,這是大多數宗教人士的起點;然而,多數的人後來不是分了心,就是把信息和傳信息的使者混淆了。好比說,《塔木德》(Talmud)寫道:「打從聖殿被毀之後,仍然擁有那位神聖者祝福的,除了這四肘長的《哈拉卡》(halakhah)之外再沒有別的了。」(Berachot 8a)對許多猶太思想家來說,這段文字教導的是《哈拉卡》的中心地位;在我父親看來,卻是一段懺悔的文字。《哈拉卡》就跟其他宗教的核心教導一樣,只是通往上帝的載體,而非上帝的代替;是挑戰,而非萬靈丹。無獨有偶,我父親也寫到禱告必須是顛覆性的,威脅你我的自滿,而非肯定你我的觀點:「對先知而言,良知的滿足只是假正經、逃避責任。」
先知除了是我父親研究的聖經人物外,更是他生命的榜樣。我兒時最深刻的其中一個印象,便是某個星期六晚上,父親離開家去參加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在一九六五年為爭取選舉權發起,從塞爾瑪市(Selma)到蒙哥馬利(Montgomery)的遊行。我記得自己親著他的臉跟他道別,懷疑是否還有再見他一面的可能。阿拉巴馬是個可怕的地方,我從電視上看到,惡毒的警長是如何毆打那些黑人示威者,把德國牧羊犬和水柱對準了黑人小孩。就連警察都站在邪惡的那一方。我父親離開家的前兩週,阿拉巴馬州的警衛才剛對著艾德蒙佩特斯橋(Edmund Pettus Bridge)和平示威的人們痛下毒手,那是一個後來被稱為「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的日子。
塞爾瑪市遊行的偉大持續不斷帶來迴響,因為這不僅僅只是政治事件,更是一個非凡的道德和宗教事件。對我父親來說,這場遊行背後是深邃的靈性議題。當他終於回到家,他說自己:「感覺連腳都在禱告。」他惟一的懊惱,如他後來所寫的,是「猶太宗教機構再一次錯失了一個偉大的機會,用猶太教的語言來詮釋公民權利運動。有許多同樣參與在這場遊行的猶太人,幾乎都沒意識到這場運動在先知傳統中的意義。」
什麼是先知傳統?我父親這本談論先知的書,便是以研究先知的主觀意識作為開始。先知不只是來自上帝的信差,一方面傳遞祂的教導,鼓舞人們行出公義,另一方面警告不聽從這信息的下場;先知預言最重要的部分,不在於信息的內容,而在於他們所展現的宗教經驗。
一直以來,先知的宗教經驗都是聖經研究上的難題。從十九世紀中葉的德國開始,聖經的學術研究便一直受到自由派新教神學家所引導,這導致他們對先知的研究,都帶有宗教論戰的色彩。他們認為,先知的教導構築了以色列宗教發展的頂峰,但所有先知之後的猶太教發展,只是逐漸走下坡,退化成狹隘的國族主義和律法主義。這群德國的新教徒認為,真正在神學上繼承先知傳統的不是猶太教,而是基督教;先知的傳統和精神活在耶穌的教導中,而非拉比的教導裡。
到了二十世紀初,基督徒聖經學者開始區分先知的教導和先知的人格。儘管先知的教導可以連上耶穌,他們的人格卻一次又一次被貶損,一如那些密契主義者一樣,往往被學者視為歇斯底里。德國的聖經學者古斯塔夫.侯舍(Gustav Hölscher),就把先知等同於那些出神狂喜的人,從迦南的異教那裡學習如何改變意識的狀態。根據侯舍的看法,處於出神狂喜中的先知,不只是把自己視為上帝的使者,更是把自己等同於上帝,以上帝的身分說話。其他學者也強調先知是如何被上帝同化,或是把先知說成不過是上帝的喉舌。
在我父親看來,上述這種對先知的理解,在聖經中根本找不到根據,他認為主要是因為學者缺乏適當的概念或工具來理解先知的經歷。出神狂喜的特質,不論是瘋狂、被上帝同化、自我的消亡,沒有一個曾在先知的文獻中提到過。反之,他建議,先知對上帝的經驗,理當是與神聖意識的一種連結,對神聖悲憫的同感,體會到上帝對人類那深深的關懷。先知並沒有被吸進上帝裡面,失去他們自己的人格,而是透過他們敏銳的情感,分享了上帝的悲憫。他們不但沒有因此失去自我,先知的親身經驗更活化和豐富了與神聖意識間的關係,讓他們在傳講上帝的信息時充滿了色彩。
本書首次在一九六二年以英文出版,發展自父親的博士論文〈先知的意識〉(The Prophetic Consciousness),那是他二十五歲在柏林大學寫成的。他在一九三二年提出了論文,通過博士資格考試,距離希特勒掌權不過幾個禮拜。為了得到博士學位,他的論文必須出版,但是在德國納粹時期,這件事對猶太學生來說一點都不容易。一九三五年,我父親的論文終於出版,出版商是克拉科夫科學學術出版社(Krakow Academy of Sciences)。這本書相當受到歡迎,不論在歐洲還是美國,都有許多學術期刊刊登該書的書評。然而,德國的聖經學者就沒有那樣的熱情。這本書出現在一個許多德國新教徒想要把希伯來書卷從基督教聖經剔除的時代,只因為那些書卷是猶太人寫的;就連認為要保留的人,他們的動機也是認為這些書卷都在反猶太,因為先知不斷譴責以色列人的罪。
我父親生活在德國納粹時期,直到最後時刻才終於逃走,他的母親和三位姊妹全都住在波蘭,最終遭到納粹殺害。這些經驗使得他在信仰上有更深的委身,也總是對那些受苦的人有高度的同情。他常常說希特勒和他的爪牙之所以能獲取權力,靠的不是機關槍,而是語言;透過語言,他們貶低了人類的價值,於此同時也鄙視了上帝。我父親曾這樣寫道:你不可能既敬拜上帝,卻又把人類貶低成像是動物一樣。特別的是,他認為德國的基督宗教領袖,對與納粹政權同夥的許多行徑都負有責任,他們沒有提供神學的工具來抵抗反猶太主義。
感謝上主,我父親逃離了歐洲,正如他後來所寫的,那經驗就像是「從爐火中抽出火炬」;一九四○年三月,他來到了美國。這次逃亡受到希伯來協合學院(Hebrew Union College)院長摩哥斯坦(Julian Morgenstern)的幫助,我父親後來也在那裡教授了五年的課程,直到他成為美國猶太教神學院(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教授。
我父親成長的世界,如今已不復存在。一九○七年出生於華沙,他是家裡最小的孩子,有著兩位很特別的父母親。我的祖父是哈西迪(Hasidic)教派的拉比,也以佩爾佐維茲納(Pelzovizner)拉比的名號為人所知;祖父的會眾絕大多數是貧窮的猶太人。我的祖母則是一個敬虔的人,許多人會請她為他們禱告,一如請拉比禱告那樣。父親的家族在猶太世界裡,可說是非常受到尊重,出過許多傑出的哈西迪領袖和思想家。當父親還是小孩子時,甚至受到有如王子般的待遇,當他進到房子,成年人皆會起立,因為知道他有一天會成為拉比。他被視為「伊魯宜」(illuy)或是天才,儘管還是孩童的時候,他就已經可以上桌分享所學到猶太經典的種種。圍繞在他身邊的人,一個比一個敬虔且持守著宗教禮儀,誠如我父親後來說的,在這樣一群富有靈性的人中間長大,讓他非常感激。
青少年時期,父親決定接受世俗的教育,他在維爾納(Vilna)完成了中學學業,並且成為一個意第緒(Yiddish)詩社的成員,他們都自稱為「年輕的維爾納」(Jung Vilna),我父親甚至還出版過一小本詩集。後來他離開了維爾納,前往柏林就讀大學,先是在改教運動的猶太教研究高等學校(Hochschule für die 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學習用科學方法來研究猶太經典;也在正統的拉比神學院修課。從某方面來說,柏林在當時也算是歐洲最有人文和知識氛圍的地方,但我父親卻發現他大學裡的教授,是如何迫切需要認識猶太人對聖經的理解。他常告訴我,當時有位教授把以賽亞書裡「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這句話,解釋成抄寫上的錯誤,這位教授認為是當時文士在抄寫經文時,忘了自己已寫過安慰這個字,所以又重覆再寫一次。我父親總是會搖搖頭要我想像一下,當年那是個如何對聖經詩詞缺乏感受的年代。
我父親用「神聖的悲憫」這個詞,作為整個先知教導的神學核心,其實是從「更高、更神聖的需要」(zoreh gavoha)這個拉比的概念而來。他堅持,上帝絕對不像傳統中亞里斯多德所說,是一個超然、永遠不動的推動者;而是「最容易被推動的推動者」,深深受到人類的行為影響。神聖的悲憫指的是上帝持續參與在人類的歷史當中,而且這樣的參與是帶著感情的投入:當人類受傷,上帝也會受苦,因此,當我傷害了別人,我就是在傷害上帝。
所以,先知絕對不是一個信差、一個口諭、一個先見者,也不是出神狂喜的人;先知是神聖悲憫的見證者,見證上帝對於人類的關切。我父親強調,上帝絕對不是一個人類感興趣的研究主題;反之,我們才是上帝關注的客體。是因著被上帝對人類苦難的悲痛所抓住,才讓先知彷彿被折磨給淹沒。面對無情和冷漠,先知並非把上帝視為安慰和暴政的來源,反之,上帝不斷對我們提出要求:「儘管世界安歇沉睡了,先知卻感受到從天而降的震撼。」
就在本書出版後沒多久,我父親就積極參與在反戰運動中;一九六五年,他成立了「關懷越南的神職人員與平信徒組織」(Clergy and Laymen Concerned About Vietnam)。正如塞爾瑪市的遊行,對他來說這同樣是一次宗教經驗,對於政治上的邪惡,卻激不起任何宗教人士的憤慨,實在是不可思議。公義並非只是一個概念,或是一個名詞;公義是神聖的悲憫。彷彿在回應先知的聲音,我父親宣稱:「談論上帝卻對越戰靜默不語,是褻瀆的行為。」如果我們真的想要與先知同感,追隨那神聖的悲憫,不論如何謹慎,我們的宗教都要被理解成是對冷酷無情的反抗。他寫道,和良善對立的,不是邪惡;和良善對立的,是冷漠。的確,我們的人性就在於我們的同情和憐憫。講到反戰,我父親說:「要記得,無辜人的血永遠不會停止哭泣。一旦這樣的血不再哭泣了,人類也就不復存在。」聆聽無聲的痛苦,並非限於先知;這任務也同樣交在我們每個人手中,正如我父親在本書開頭所寫的:「少數人犯罪,但所有人都有責任。」
東南亞的越戰讓我父親心力交瘁,直到他過世(他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離世)前,有好多個夜晚都難以成眠;他竭盡全力要讓這場殺戮劃上句點。他的好朋友丹尼爾和菲力比.貝里根(Daniel and Philip Berrigan),這兩位天主教神父都因反戰入獄;威廉.科芬(William Sloane Coffin),當時耶魯大學的牧師,也被指控是焚燒徵兵卡運動背後的主謀。父親沒有實際參與公民不服從運動,因為覺得在監獄外面,他可以更有效參與反戰運動。他在無數抗議場合講過話,也在每一次的授課和演講中談到越南的問題。上他課的學生,在對先知有更多認識的同時,也會聽到與戰爭有關的教導。
我父親其中一個醒目的領導特質,便在於他對自身群體的批判精神。正如為種族主義和戰爭的發言一樣,他也同樣批判著猶太宗教機構:「每一個安息日,總有許多猶太人聚集到會堂來,然而,他們離開時,卻和剛進來時沒有什麼兩樣。」禱告似乎變成間接、替代性的事,委託給那些「根本不懂靈魂語言」,也不知如何激勵人心的拉比和領袖。他除了在正統、改革且保守的猶太教派中找到問題,也同樣在平信徒領袖和負責教育的人員中,看見許多的問題。太多的錢都花在人數的統計與調查,而不是教育的事上——儘管負責教育的人,原應要重新將「尊重學習和學習尊重」作為他們的目標。敬拜的人失去了對神該有的敬畏,聚會彷彿變成一個社交場合,而非神聖的時刻。整個社會都在崩解,猶太教卻跟著衰敗,而非提供整合的資源。我父親寫到,本該是暮鼓晨鐘的猶太教卻成了陳腔濫調;當代的猶太人,是一群忘了信息內容的信差。
這樣的批判使得他在猶太群體中並不受到歡迎;直到今天,許多猶太人依舊喜歡世俗的信息,而非宗教;把自己視為受害人,而不是有責任參與政治的行動;只說猶太教的好話,卻不做任何批判。我父親從來不說聽眾想聽的話,而是告訴他們需要改變。正如先知一樣,邪惡從來就非歷史的高峰,父親的信息有時雖然嚴峻,但始終抱持著願景和盼望:「那超乎你我感受、讓人驚艷不已的更新終會來到,我們將對生命恢復崇敬,意識到自己最終的不足與虧欠。」
新書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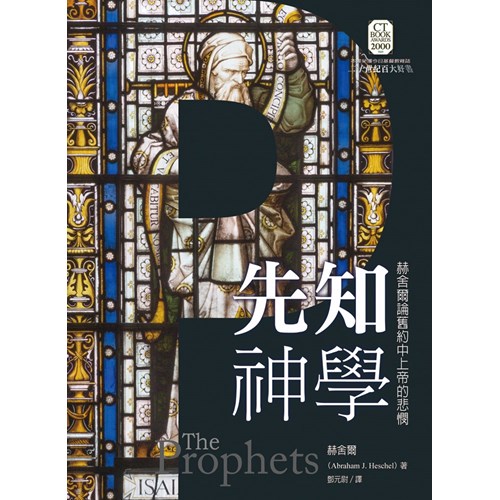

 線上試讀
線上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