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本售價:140元

當許多國家的政治、社會、文化氛圍愈來愈對立,人際互動也就有了更多問題。不同社群間誤解、衝突的常見原因之一,往往在於過分簡化另一方。儘管我們理性上明白「刻板印象」有害無益,卻依然不自覺地給非我族類輕易戴上面具、掛起標籤:美國人都是餐餐喝可樂的?中東來的大鬍子客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亞裔學生都是功夫高手或數學天才?
分化與對立的問題,並不只在政治社會的大範圍檯面上,只要有人,就有紛爭。當學生反目成仇,來跟我告狀時,通常雙方使用的詞彙驚人類似(我是何等忍耐退讓,對方是何等無理取鬧、暗箭傷人……)—然而,如果雙方都真如自己所說的忍耐、退讓、體諒、願意溝通,又哪來的種種紛爭?
從公共領域到私人空間,為什麼我們這麼容易分黨結派、畫界線畫圈圈,這麼輕易不把對方當作和自己相似的人—複雜、軟弱、有夢想、會犯錯的人?
是不是把「對方」妖魔化,我們就不用面對自己裡面的邪惡?
是不是把「對方」踩在腳底下,我們就容易活在自己假想的高度上?
我和我身邊的少年,迫切需要學習—學習如何在這個衝突動輒激化,種族動輒對立,同儕動輒干戈,敏感的政治離間了家人朋友關係的世界(二○一六年美國希拉蕊和川普激烈選戰後,許多美國人與支持不同政黨╱政客的親友鬧翻了,半年、一年不說話的比比皆是),走出一條和平互動的道路。
如果單一族裔背景的人們,面對「非我族類」常有理解和溝通的困難,那麼北美近年成長快速的跨種族通婚家庭,他們的下一代,是不是自幼就要在筷子與刀叉(或其他餐具)之間練習平衡?從小聽著幾種語言成長的孩子,會不會更有希望找到世界共通的新人際語言?
擁有兩種族群身分(也可能兩邊都進不去)的混血兒,從出生到長大到成人,天天在不同的語言文化裡學習與掙扎,他們的故事,對我們應該別具參照價值。
小說是寶貴的(即使有點搖搖晃晃)吊橋,讓我從自己熟悉的語境和文化處境,走向陌生的彼岸,走入從來沒有造訪過的天地。最近跟著兩本青少年小說,我認識了現實裡沒機會接觸的種族文化,隨著少年大流士腳步遲疑地去伊朗旅行,和少女瑞秋擺盪在芝加哥和波特蘭兩個個性如此不同的都會,發現異文化沖激出來的水花,居然有我能指認的彩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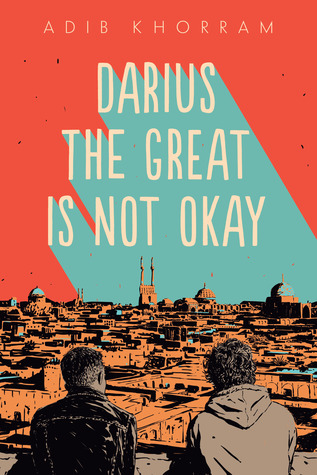
高中十年級的大流士,屬於美國成長最快的族群之一,是填資料表時,種族欄目屬於「其他」的那群。持平來說,他是多族裔混血兒,說難聽點就是,他不是純種。母親從伊朗來美國留學,認識了北歐裔父親。兩人成家後定居北美,一年後有了大流士,再過八年有了妹妹蕾拉。
歷史書裡的大流士大帝,是古波斯王國偉大的君王。
現實裡的大流士覺得自己什麼也不是。
他不屬於每天上下學的波特蘭郊區高中主流社群—就算裝作若無其事,天天找機會欺負他的同學,也會不斷提醒他是個異類。
他也不屬於傳統波斯文化。妹妹蕾拉能用流暢的波斯語和外公外婆視訊聊學校大小事,他的波斯語和爸爸一樣只限幾個單字。
更糟的是,他是讓建築師父親持續失望的根源,從他的頭髮到他的體型到他的成績到他的個性到他的憂鬱症,爸爸對這個長子似乎沒一樣滿意……大流士心想,難怪爸媽隔了那麼多年才有第二個孩子—他這個先發嘗試太失敗了。他感謝上蒼,蕾拉在任何一方面都是他的升級版本!這麼完美的妹妹他沒法嫉妒,只能全心全意地疼愛她。
春假前傳來消息,外公腦裡長了瘤,不知道還能活多久。幾週後,他們全家上了飛往伊朗中部城市亞茲德的飛機。從沒當面見過外公外婆,痛恨長途飛行的大流士,一路擔驚受怕,卻沒料到這將是一趟深度發現他人和自我的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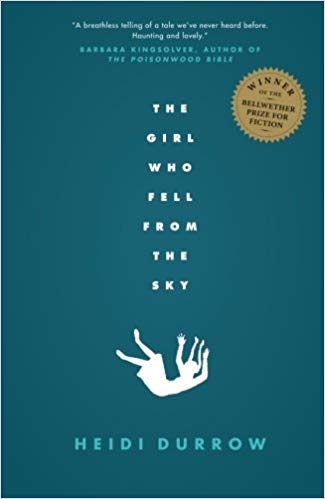
瑞秋父母的戀愛故事有一點像童話:英俊的非裔美籍軍官駐防歐洲時,和豆蔻年華的丹麥姑娘結為連理。身為軍眷,媽媽帶著瑞秋和弟弟,跟著聽憑部隊調動的爸爸,在歐亞各個基地東遷西徙。小時候她沒細想,為什麼爸爸這麼少帶他們回美國老家?為什麼她幾乎不認識爸爸那邊的家人?
隨著瑞秋成長,爸爸酗酒問題愈來愈嚴重,父母關係漸漸走下坡。不耐寂寞的母親有了婚外情,她相信這個男人會給她一個全新的未來—即使這表示她要帶著三個孩子從歐陸橫跨大西洋,來到人生地不熟的芝加哥。幾個月後,瑞秋全家成了地方新聞頭條。諷刺的是,母親和兩個弟弟永遠無法睜眼讀到這條新聞了,而躺在醫院加護病房的瑞秋也看不到。
瑞秋昏迷不醒時,生父守護床邊,然而害怕自己會搞砸父親角色,他又再一次離開,把瑞秋託付給在波特蘭的母親和妹妹。
(當十二歲的妳,醒來發現自己是母親和她三個孩子的跳樓悲劇—意外?謀殺?自殺?—的唯一倖存者時,活下來的妳,會有一絲一毫的興奮嗎?)
來到波特蘭黑人區的瑞秋,不僅要默默咀嚼劫後餘生的滋味,重組支離破碎的內在生命,還必須適應環境和全新的外在挑戰:一個有著海藍眼睛、咖啡色皮膚的孩子,如何在非裔和白種群體兩邊的壓力推擠下,找到自己的形狀?
她的外婆完全不提早逝的媳婦,想要瑞秋長成一個非裔窈窕淑女。但是「非裔」就是膚色、髮型、口頭俚語的總和嗎?「丹麥人」就是母親以往常用的生活單詞和家鄉點心的積聚嗎?
瑞秋在墜樓慘劇後,必須重建她的身分認同,在種族的巨大張力間找到平衡點—這不是教科書上的討論,而是她每一天的現實生活。她試了不同的方法,從壓抑自己的情感與想法,到假裝自己是百分百的非裔,到重新面對自己複雜的背景,以及意外背後母親的情緒深淵……幾年過去,瑞秋夢裡無止境的墜落,總算暫停。也許,她可以慢慢爬出種族間的鴻溝,也許,有一天她可以自由飛翔。
來到伊朗中部古城的大流士,因為祖母的溫暖疼愛,和生平第一個好朋友的接納,開始看到自己承襲了值得驕傲的傳統。因為與長輩和同儕有意義的接軌,他的靈魂終於不再浮游,扎根後,開始茁壯。
大流士和瑞秋的故事極其不同,然而對於種族議題,還是可以找到一些連結:
一、面對現實
種族文化的問題非常複雜,不是一兩天、一兩句話就可以搞定。然而假裝問題不存在,絕對不會讓問題自動消失。瑞秋、大流士以及他們身邊的家人,都選擇過逃避現實,小心翼翼地活在自己的角落;而故事的轉機,也都從他們願意爬出洞穴,在刺眼陽光下好好正視自己和他人的現實開始。
二、困境解套
1. 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慢慢地指責、慢慢地批評……):瑞秋在找到抒發管道之前,曾經想像自己裡面有一個藍瓶子,她把一切的憤怒、憂傷、不解,一次次裝進瓶子裡,再嚴嚴地栓上瓶蓋。我們身邊許多的邊緣少年,裡頭也有這樣一個瓶子,等待一個願意聽、不願意定罪的人,等待一個適當的時間,讓他們可以打開瓶蓋,傾吐點滴心事。
2. 一起做一樁事:大流士到了陌生的亞茲德,和剛認識的鄰居少年一起去公園踢足球,共同的遊戲經驗是他們友誼生發的土壤。大流士和父親多年相處不易,靠著每晚一起看一集星際迷航,讓兩個不善言辭的人開始有了共通詞彙,有可以數算的回憶資產。在我們和與自己天差地別的人能夠找到共同語言、進一步交心之前,起碼我們要願意和對方在同一個時空裡共處。
3. 擁抱沉默:多數人覺得靜默是尷尬的,是不舒服的。然而當我們還在關係摸索的階段,能夠靜靜守候、靜靜觀察,也是一種祝福。瑞秋故事裡的神祕少年,在告訴瑞秋生父託付的消息之前,忍耐等候了許久。大流士的外婆和他雖語言不通,但她以肢體語言清楚表達了她的接納。善意的沉默代表我們尊重不同背景的人—如果我們張口只想傳遞自己的優越,或是傾倒一長串問題,那麼我們或許該學習靜默觀察的愛語。
4. 接納過程:大流士故事的英文書名在尾聲時有了不同意義,因為他終於領悟到,生命中許多挑戰不是一蹴可幾的,父親和他多年的憂鬱症、外公的腦瘤,不見得有魔法可以解決—可是他接納了自己與別人的不完美(It’s ok to not be ok),這份接納是成長的下一步,也是走向偉大的過程。
我所處的學校有許多社區服務機會,其中一個叫做「愛心洗衣間」。參與者固定在一個投幣洗衣店,帶著銅板和笑容,服事街友與低收入家庭洗衣、烘衣。數月前,我帶著幾個國際學生第一次參與,我有些忐忑:這個區的社經條件顯然不太高,排隊等候的街友不是常見的族群,洗衣店的投幣式機器她們從來沒操作過……。
然而,這幾個嬌滴滴的少女,卻超出我的期待:認真服務了三小時,手沒停歇過,臉上始終帶著真摯笑容。回程車上,一個孩子說她心裡有些難受,因為一個婦人英文口音重,語速又快,她拼命想聽懂,還是沒辦法完全理解。另一個孩子說,幾個銅板的洗衣費,他們要排隊等半天,等到了還一直道謝,讓平常完全不把這種小錢看在眼裡的自己,忽然發現25分硬幣的價值。另一個又說,那些跟著媽媽來的小小孩好可愛啊!我想學西班牙文了。
手握方向盤默默開車的我,被這些孩子願意走出自己的舒適圈深深感動。遠離日常的投幣洗衣坊,不也是多元社會的另一層縮影?多來幾次,我相信她們以後遇到「瑞秋」,會從心裡接納她特別的外貌與更複雜的內心;假設和「大流士」照面,也不會立即貼上隱形標籤。
當我們願意嗅聞不同地域烹調的特有氣息,嘗試把陌生菜色放進嘴裡咀嚼;當我們從閱讀中、在生活裡愈來愈體會,每一個人都在自己和他人的文化夾縫裡交錯拉扯;當有一天,我們看到鄰舍有緊急或長期的需要,期待我們的眼光可以超越種族,驅動我們停下腳步,伸出手,打開錢囊,練習愛的功課—
地球村的時代,我們不都是彼此的鄰舍嗎?
從古到今的歲月,祂不一直都是我和你的鄰舍嗎?
對鄰舍,祂只有一個字的命令,值得我們這些不OK的人,一輩子學習。
當期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