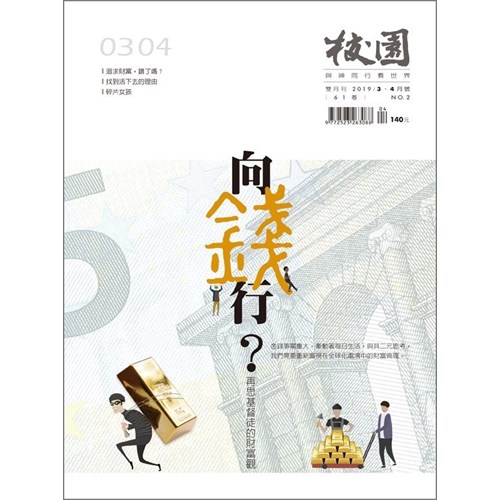
每本售價:140元

大部分時候,我們表面似乎過著歲月靜好的日子。即使下頭有暗潮湧動,我們仍戴著面具,用妝容服飾來堆砌他人眼裡的綠地晴天。天地若沉默,世界不會拿著放大鏡追問,學會帶著白雲般的鬆軟微笑,就更能讓他人放心。
直到地震海嘯、火山爆發,天塌了一邊,妳忽然發現原來自己的保護並不周全。太平盛世是個紙糊的影戲?
在來美國念書之前,妳是喝西北古城奶水長大的孩子,直髮和大大的眼瞳一般漆黑,眉眼帶著幾分古典婉約,同學半開玩笑地說,穿起漢服妳應該可以直接「穿越」。教室裡,妳坐在角落,幾乎不主動說話,老師點到妳回答問題,妳的回應總是簡短又客氣。
開學不久,我努力認識高一新生和今年特別多的轉學生,那些明顯傷腦筋的孩子快速跳入我的特殊關注排行榜—比如開學第三天就偷偷跑到校門外抽煙的那一小群,還有六門學科全部不及格的新生。但沉靜乖巧的妳並不在名單上。我想,妳應該不需額外照顧,有時間再慢慢認識妳。
直到那天上午電話響起,個性穩重的秘書的聲調不像平日:「嗯,抱歉打擾了,在生物實驗室裡老師注意到……可以嗎?好,我帶她過去。」幾分鐘後,高中秘書帶著妳走進我的辦公室。
妳低頭不願直視我,披散下來的烏黑髮絲遮住大半臉龐,我只看得見妳斑駁的唇紅。壓抑住心裡翻騰的情緒和彈跳的問號驚嘆號,深呼吸、壓低聲音問妳,願意和我談一談嗎?
幾乎看不見似的,妳輕輕地點了點頭。
接下來一個多鐘頭,像一瓢隱藏的泉水,當我小心翼翼地提問,敲開了表層土石後,妳滔滔流出了心事和故事。
那天以後,我有了新任務。上網查了自殘的各種資訊、和心理諮商師請教、和寄宿家庭長洽談、和校長會商、和老師們一同禱告、常常直接間接關注妳。但總覺得還少了點什麼,還能再為妳做點什麼呢?
想要更深地觸摸妳傷口的溫度。想要更理解妳生命地表下面的板塊撞擊與斷層。
就像過往,當發現自己對身心某種傷痛所知有限時,我便搜尋閱讀相關小說。有時所謂虛構的故事,往往更靠近真實。
收到快遞來的《碎片女孩》(Girl in Pieces),一個陌生作者的首部長篇少年小說。等不到週末,我打開了這本書。
當我被書裡赤裸裸的描述刺痛到掩卷閉目時,妳的影像鼓勵我繼續讀下去。妳對我—一個才認識不到兩個月的國際生學術輔導—的傾心信任,激勵我,在自己車禍後的療養之路和學校、家庭團團轉的忙碌中,讀完了《碎片女孩》。
故事開場時,查莉十七歲,然而她經歷過的難處,比有些人一輩子經歷過的還要多:失去了童年時溫柔對待她的父親(長期憂鬱症後投河自殺),身心俱疲的母親對她只剩忽視和虐待,在學校面對長期的霸凌,高中唯一的朋友在生死邊緣掙扎……還沒完!她被趕出家門,流浪街頭,受毒犯控制,出賣身體…… 還沒完!她掉進憂鬱症和反覆自殘的深淵,最後自殺未遂、被街友送進明尼蘇達精神病院,還沒完!住院四十五天後療程被迫中斷,她上了灰狗巴士,目的地是亞利桑那州,幾千哩外的沙漠城市土桑,為要投靠多年不見的朋友。才剛步上恢復之路,才剛開始學習如何用健康方法處理負面情緒的查莉,有可能在全然陌生的地方調整步伐再出發嗎?
曾經,當世界和她自己都被黑暗浪潮淹沒,查莉唯一的出路是一條血路,並不是殺掉自己,一了百了,而是用皮肉痛楚來懲罰自己,卻同時也釋放自己。
這種處理,聽起來不理性、不邏輯又不健康,怎麼會有人選擇這樣處理負面情緒?
可是,來自萬里之外,文化語言經歷都和查莉不同的妳,卻說了和書裡心情類似的話:
「老師請一定要相信我,昨天晚上我沒有半點要自殺的意思,可是掛了電話我坐在書桌前,孤伶伶的,我好想好想家,我好擔心好擔心我爸爸,我覺得自己快頂不住了……老師,那種痛我真沒辦法形容,像海浪一樣,快不能呼吸了,然後我就看到抽屜裡那把……。」
妳說,妳並沒有太多次傷害自己的經驗,算是自殘部隊的新兵?(我巴不得妳立即退役,再也不加入這支隊伍,但也知道如果不陪著妳慢慢身心復健,事情不會那麼簡單。)
故事裡的查莉,比妳大不了兩歲的查莉,在生活的艱難困苦裡想存活下去,已經是裡外傷痕纍纍的老將,落到情緒低谷時,玻璃碎片是武器,她在自己的身體上留下一條條不光榮獎章。
妳和查莉,和許多不知如何面對世界、面對自己的孩子,寂寞是你們日夜呼吸的空氣,你們是在用肉體上的疼痛來對應心靈上的疼痛啊!
查莉說,自殘過程中最「好」的部分,是當她一絲不苟地消毒、包紮傷口時,會升起一種難以形容的滿足感—至少在這混亂無比的人世間,我還有這點把握,還有這點控制,可以選擇在哪裡切割自己,知道怎麼包紮傷口。
然後呢?短暫釋放後,所有沒解決的問題還是在那裡。只是現在多了得隱藏起來的傷疤。
就像查莉,妳總穿上長袖上衣,不只是愛美、怕曬,而是怕這些私密戰場上的傷疤暴露在比陽光更強的眾人目光之下。
就像查莉,妳最怕被人發現妳偷偷傷害自己的祕密。但矛盾的是,妳又默默渴望有人看見—只要那個人看見後,不會掉頭就走。
《碎片女孩》的作者凱瑟琳.格拉斯哥(Kathleen Glasgow),花了九年七個月的功夫寫這本書。定稿前梳理了十三次草稿。寫作十年間她失去了摯愛母親和姐姐,自己也做了母親,兼顧撫養幼兒與全職工作,還跨州搬遷……為什麼重重困難中她沒有放棄這個故事,為什麼她沒有掉頭離開查莉這個支離破碎的女孩?
這要說回故事的種子:多年前在明尼蘇達州雙子城公車上,那個偶然落坐在格拉斯哥旁邊的少女。當時格拉斯哥一眼就瞥見女孩手腕上的猩紅刀痕,驚慌失措的女孩覺察到她的注視,慌忙拉下袖子,一路正襟危坐,直到她到站下車,兩人沒有目光交換,也沒有說話。
然而那段公車路程上,格拉斯哥心裡一次次吶喊:「嘿,看看我,要是我捲起袖子,你會看到我也有(過)!」
多年後,這部不管怎樣難產也要生出來的小說,就是受那次讓她事後後悔的沉默驅動,是她內裡那些無聲吶喊的回聲,是一個年少時走過重度憂鬱、酗酒成癮、自傷自殘,好不容易存活下來的作者,對那些自我傷害的孩子,還有他們不知如何是好的父母與朋友堅定地伸出帶著傷疤的手。
查莉遭遇如此悲慘,裡外如此殘破,活下來都不容易,還能奢望活得精彩嗎?
在一大片黑暗森林之中迷了路受了傷,只要有一隻鳥唱歌,就有走出黑暗的盼望?
是,尤其如果你自己就是那隻唱歌的鳥。
我願意靠著祂的恩典,作一根讓妳可以棲息的枝子。
即使妳的傷口讓我夜裡想起流淚,妳的缺席讓我坐立難安,妳成績下滑,我和老師一個個溝通,這些「麻煩」都不是我期待的,但遇見了妳,我願意承擔。我聽過妳次數不多的笑聲,相信妳看來混亂的生命泥土裡,有一千個愛的種子期待發芽。
查莉畫畫,不停不停地畫,畫畫是她的歌聲,一筆一劃帶她走出暗林。
格拉斯哥寫文章、寫詩、寫故事,不停不停地寫,文字是她的歌聲,一字一句,帶她走出幽谷。
上帝擺在妳裡面的熱情又是什麼呢?妳會為了什麼不止歇地歌唱?妳說妳什麼都不特別喜歡,那是不是表示妳還在尋找?
有時難以對外界解釋,高中國際生學術輔導是我做過最波濤起伏、最有挑戰性的工作了,誰說校園生活平淡無奇?你們的背景殊異、適應艱難,面對的、製造的問題也高潮迭起,向來愛平靜不愛刺激的我,怎能一路待到了第六個年頭?
因為妳。
因為即使我的身體沒有看得到的傷疤,在我的生命年輪裡,也有和妳相同的傷口—十六歲的我懂得妳的痛、妳的孤單,懂得妳在同學面前選擇戴上面具;二十三歲離鄉背井的我,也嚐過在星空下痛哭想家的滋味;四十歲依然被家人的話重重刺傷的我,也曾經拿起剪刀把眼前的信封剪得細碎,極度控制自己不讓刀刃剪進皮肉。
我用我全部的生命經驗想讀懂妳,用各種閱讀來與妳靠近,那些遠遠不足夠的地方,我知道祂可以,祂完全承擔我們的軟弱,擔當我們的憂患,醫治我們的傷口。
查莉的故事,妳的故事,多少孩子的故事,不必再留在黑暗角落,不必再用長袖遮掩。
妳在這裡還有幾年,我和老師們願意做一棵樹,邀妳棲息,直到妳明白不需要為自己造紙糊的藍天,也不需要在受傷的羽翼上塗抹厚厚彩妝。
直到妳可以加入這首歌的和聲:
Every tear, every doubt
Every time you've fallen down
When you're hurting, feeling shame
When you're numbing all your pain
When you've lost your way
And feel so far away
You're not
You're beautifully broken
And you can be whole again
Even a million scars
Doesn't change whose you are.
直到妳真正遇見那已經把新歌寫在妳靈魂深處的耶穌。
在祂愛的天空裡,帶著傷疤的妳,永久屬於祂的妳,將學會飛翔。
黃瑞怡
當期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