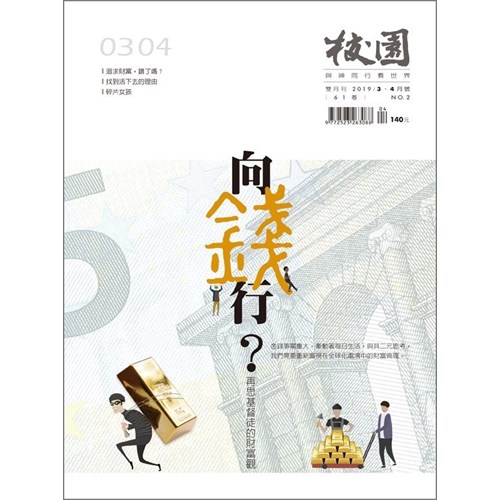
每本售價:140元

現代人處在一個極度商業化、資本充斥、物質豐富,又自由開放的社會裡,即使身為一個敬虔的基督徒,追求財富,其實沒什麼不對!真正需要在意和執著的,毋寧是在追求財富的背後,賴以支撐的合宜動機、責任和價值信念。在以下的篇幅,筆者的主旨很簡單,就是要辯明此一道理。
首先,對於財富的積極進取,第一個好理由是現實和角色上的需要。先從現實上來說,無論出國進修、成家、買房、子女教育、家庭旅遊、退休養老,或醫療長照等,都需要相當可觀的錢財,累加起來更是驚人。而殘酷的現實是,在很多城市裡,物價、房價、學費、醫療就是那麼貴,即使你有千萬個意願和決心要儉樸,卻由不得你。這意味著,個人層次上的儉樸意願和決心,還得要有社會條件來配合;除非你有選擇居住城市的充分自由。
再從角色上的需要來說,就算你在現實上有條件可以儉樸,但為了將自己的角色功能扮演好,你可能需要比較昂貴的消費、體面高檔的生活方式,甚至有點闊綽的低調奢華。這番話乍聽起來,恐怕讓不少基督徒存疑或搖頭,因為它非常不正統!但其實,我們只是太習慣於儉樸的標準答案罷了!
儉樸的鼓吹者總是強調,錢財只要能維持基本需求就夠了!但卻忽略,每個人的基本需求有很大差異;而它未必是主觀慾望的問題,往往是各人所屬的不同階層、身分和角色所致。譬如,文人或教授的基本需求,顯然與基層的勞工和農民不同。他通常需要購買大量的書籍、寬敞的書桌,並藉由旅行和藝術等文化消費,來培養視野和見識。但這一切對勞工或農民來說,卻往往是多餘的。深究起來,其中存在著一個非常關鍵的動機因素,即他們不是出於一己的私慾或虛榮,而是為了將角色功能扮演好。
曾經有位會計師朋友告訴筆者,雖然他個人崇尚極簡主義,卻選擇以賓士汽車代步,因為在其社交圈中,這樣比較容易爭取到客戶。持平而言,此一論調不無道理,寬敞闊綽的辦公室、出入高檔的進口車、品味典雅的擺飾和衣著,可以強烈傳達一種成功人士和專業菁英的暗示。這就是角色功能上的需要。
還有一位在信仰上很追求的姐妹,曾經長時間在國際時尚品牌擔任執行長,她向筆者透露,當時她全身的穿著打扮,通常至少幾十萬的價碼。對她來說,這一切並非出於自己的私慾或虛榮,而是以她的階層和身分,在領導和公關上的需要。
阿奎那和馬丁路德的看法
其實,這樣的道理在十三世紀,神學泰斗阿奎那(T. Aquinas)早已提出來了。當談到施捨時,他強調, 有些必要的東西是維繫「社會地位的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如果施捨到一個地步,以致所剩下的東西「不足以過一個適合自己地位和應付日常事務的生活,這是不對的。」[1]
在這番話中,阿奎那明顯強調了資財在維繫社會地位上的重要,只是他還沒有切入角色功能的視角。之後的馬丁路德就在這一點上加以闡揚了。他說,雖然「金錢、財產、名譽、權力、土地和僕人」都屬於世俗的範圍,但「若沒有這些,世界不能持續下去。」而既然它們不可或缺,那清貧或僅僅溫飽就不恰當。他坦然直言,「一位主人或公侯不應該、也不能貧窮,因為基於他的職務與身分,他必須擁有這些東西。」[2]
一來,身為公侯,所需要的宅第、護衛、威儀、排場、衣著和文化品味,當然與勞工或農夫有不少的等級差異。而作為一個主人,除了妻小,還有眾多僕從的家庭要顧養。
二來,公侯或主人所擁有的莊園、農地或工廠,不只得持續投資、營運和維護,其背後更經常牽連到社會的某一部份政經體系,需要公侯或主人去扮演好領導或管理的角色。
基於這兩個理由,他們豈能沒有可觀的資財來支應?坦白說,那種但求溫飽的主張,恐怕只適用於鄉居或修道院的隱士、退休老人家、家庭主婦,或底層階級的人群。他們的共同特色是,沒有什麼階層或身分上的角色需要扮演;通常,他們只要作自己就可以了!
反過來,則另有一大群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人口,尤其是領導菁英、大小企業主、經理高管、社會賢達,以及各個不同領域的專業工作者,得為了階層和身分上較昂貴的開銷需要,而在財富的追求上積極進取。
據此,一個小小的結論出來了。到底一個人需要多少財富呢?這當然沒有標準答案,但其中一個指標,就是根據不同階層和身分的角色需要,來擁有不同程度的財富。
角色需要也有其規範
只不過這個指標在應用上要謹慎,它有個附帶但書。一方面,許多人的需求不可能只侷限於基本溫飽就夠了;另一方面,卻也不當超過角色扮演上的必要。換言之,角色上的需要,既是致富的一個好理由,也是致富的一個自律性規範。
譬如,一個教授開幾百萬的高級名車、普通員工出手闊綽的奢華消費,或公務人員卻住豪宅又全身昂貴精品,這一切顯然已經逾越了各自在階層和身分上的角色需要,毋寧為一種驕暴。
遺憾的是,這種情況即使在理應敬虔的教會史中也屢見不鮮!中世紀的教皇們就經常聲稱,所享有的一切威儀、排場、尊榮和奢華,都不是為了一己的私慾和虛榮,而是為了彰顯和榮耀自己所服事的上帝—萬王之王。換言之,它們都是基於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身分而有的角色需要。
結果,就如馬丁路德所描述的,一般的國王頭戴一重皇冠,教皇要戴三重皇冠,還配屬了三千個秘書;出外遊樂時,則安排有四千人騎驢子的隊伍;並且,這位超級神僕還拒絕乘馬坐車,堅持要像個偶像般地被抬上轎子。
對於教皇的這一切所為,阿奎那沒有批評。但馬丁路德可不以為然,他大肆抨擊其為腐敗和墮落。尊榮和禮遇教皇,固然是一種角色上的必要,但何以竟表現為「聞所未聞的浮華」和「耀武揚威」的傲慢?[3] 顯然,它們已經過頭了。
迄今,教皇的那一套藉口,輕而易舉地在資本主義的腐蝕下找到了許多知己。譬如,曾經風靡美國的許多電視佈道家,坐擁鉅額資產、豪宅、遊艇和私人飛機,他們所抱持的理由,除了成功神學外,不就是因自己所服事的乃萬王之王豈可寒酸嗎?換言之,這一切都乃根據其特殊地位和身分所必要的尊榮,其本質毋寧是榮耀上帝,而不是出於一己的私慾和虛榮。
這可真是一個麻煩!主張財富應該要符合階層身分、職務或角色的需要,反而為私慾和驕暴找到了一個好藉口。但儘管如此,筆者還是要說,對於財富的積極進取,這仍是一個在倫理上的好理由。畢竟事物都有其兩面性,天底下可沒有什麼主張是天衣無縫、毫無漏洞的。
只是,這中間的尺度又該如何拿捏呢?它同樣沒有標準答案,總因人因時因地而有很大差異。或許有人會認為,該取決於各自所屬群體中一般性的角色期待。然而,這卻存在著隨波逐流的世俗化風險。唯一的更美之道,恐怕只有抱持著中道原則,並自己在靈裡面儆醒了。筆者始終相信,在所有的兩難抉擇中,那最美好的尺度,總是只存在於一顆敬虔活潑的心靈裡。

談過了現實和角色上的需要,進一步地,對於財富的積極進取,第二個好理由是擁有尊嚴和自主能力;即財富可以讓人免於被支配,從而自由地選擇所期望的生活。
當然,從我們基督徒來看,要過在地如在天的好日子,最需要依靠的是上帝。但我們不當忽略,從物質條件來看,許多人因缺乏經濟能力而失去了選擇的自由。他們不能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只能淪為滿足別人生活的工具。當你看到底層的人們爆肝、沒命地工作,甚至得將兒女交給住偏鄉的年邁父母去養育,你就知道上述所言不虛。那完全不是他們想要的生活,但卻很無奈。類似情節的故事,在低度開發的國家裡尤其普遍。
金錢邪惡的支配力量
許多人常錯誤地認知,以為金錢最糟糕的用途是奢華浪費,其實它最邪惡的是用來支配他人、使別人淪為奴役。譬如,員工為五斗米而向跋扈的老闆折腰;丈夫用金錢來脅迫妻子順服;債主要求欠錢的人賣女兒來償還。到處我們都可以看到,大爺拿錢來支配人!
難怪!馬克思當年會帶著憤怒控訴,說「貨幣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他以此諷刺資本家對工人的支配,並指出貨幣就是一種「支配他人的、異己的本質力量」,因為它「具有購買一切東西、佔有一切對象的特性」。同時,在所有的關係網絡中,它是最重要的「牽線人」,有著巨大的權力,可以獨斷地決定要將關係予以拆散,或繫得更緊![4]
俗話不也常說,「有錢才能做人!」它帶來的正是一種權力在握的受歡迎感。那沒錢呢?就往往陷入被決定、孤立或邊緣化的命運。
不只如此,馬克思還宣稱,歷史顯示出一個法則,即那些掌控財富的階級,會同時掌控你我腦袋的思想!反過來,缺乏經濟能力的人,就注定淪為他們在教育、傳播、法律、道德、宗教和文化上的應聲蟲!
整個來說,馬克思呈現了一個深刻體會,即財富具有一種如神明般的魔幻力量,它進而可以支配他人,以有效滿足利己的渴望;退而可以排除他人的支配,免於被異化(estrangement),並積極地自我實現。
想一想,確實是如此。如果你口袋很深,就可以不鳥那些用錢來支配人的大爺,從而快活地作你自己!在印度,就有不少女性在擁有穩定收入後,即刻拿掉蒙臉的面罩。她們從來就不喜歡配戴,只是因應社會習俗的要求;而今經濟能力的增強,讓她們開始勇敢說不!
透過金錢,獲得自主的力量
正是基於此一理解,使得沈恩(A. Sen)這位印度裔的諾貝爾獎得主,直接將貧窮定義為「基本能力的剝奪」。這句話說得強烈卻真實!你愈缺乏經濟能力,就愈淪入一種無行為能力狀態,即任人擺佈。
他故而明白指出,我們之所以該追求更多財富,乃因那是「我們爭取更多自由的典型手段」,為了是能「讓我們擁有可以珍惜的生活」。[5] 從表面上看,我們似乎都擁有充分的權利去選擇所期望的生活,但事實上,其中的自由度總隨著經濟能力而消長。
就在你我的周圍,很多女性無法離開外遇或家暴的丈夫,其中一個常見的原因,就是自己缺乏經濟能力,結果只好忍氣吞聲。不久前,筆者才讀到中國大陸的一則笑話:婆婆想趕走媳婦,就對她說:「這是十萬,離開我兒子。」孰料這位媳婦財力雄厚,竟回應說:「這是一百萬,離開你兒子。」這番對話雖然病態,卻鮮活印證了沈恩之論!
值得一提的是,另有位經濟學者布坎南(J. M. Buchanon),很精闢地從市場的角度提出了相同見解。他說,現代社會的分工和交換都極為緊密,並造成了對他人的高度依賴。然而,這卻大幅增加了個人生活中的風險、不確定性和隱藏成本。因為總有一小撮人擁有市場的優勢和政治上的影響力,而他們對於物資和必需品的產量、價格和分配,必然擁有不公平的控制權。
這導致了你得支付昂貴的房租,或者被迫在超市購買不怎麼新鮮的必需品;還有,你得忍受不良的工作條件、配合討厭的客戶或廠商。
那該如何擺脫此一依賴、避免這些不快呢?布坎南的答案是,讓自己擁有足夠的財富,以握有最大的獨立性。如此一來,你可以自主地決定,是否要進入市場中的依賴關係;二來,你也有自由不理會市場中那些強勢者所訂出的規則。
他一再強調,愈是依賴於他人的決定,就愈容易受到他人的決定所傷害。人生的最佳選擇,毋寧是擁有更多的財富,來讓自己擺脫對他人、乃至對國家的依賴。就如在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福祉高度依賴政府;然而當政客縮減福利政策時,人民就可能受到重創。這時就突顯出,那些不依賴福利措施而能過好日子的人,是多麼幸福和具有生存優勢了。
布坎南更指出,即使市場的運作公平,沒有剝削和支配;甚至,所提供的服務相對便宜或更有效率,但許多人為了擁有更多的自主性和自由,仍寧可選擇由自己來提供服務。
譬如擁有自己的住宅和汽車,而不進入市場去購買別人的服務(租房子或搭捷運)。雖然後者更便宜又有效率,但許多人卻將自主性和自由當作更優先的價值。他們不願被迫搬到捷運站附近、得配合捷運的時間表及路線。他們喜歡住在山邊或郊區,或狂歡到半夜才開車回家。
寫到這裡,很清楚了,財富所帶來的幸福,就是實實在在的選擇自由。它不僅可以讓我們拒絕不公平、被剝削和支配,免於風險、不確定性和隱藏成本,甚至,還可以不必屈就於便宜和效率,能更自在地選擇所期望的生活。
追求財務自主的自律規範
只不過,此一好理由同樣有個附帶但書。既然致富是為了擁有尊嚴和自主能力,那也不當為致富,而犧牲一己或他人的尊嚴和自主能力。在此,選擇的自由同樣既是致富的好理由,也是致富的自律性規範。
這在現實情況裡有點複雜。有一群處於被支配地位的人,往往是無可奈何的被犧牲者。為了家庭和生計,不僅備嘗忙碌、壓力和疲憊,還經常被迫出賣自我和靈魂、只能卑躬屈膝地生活。但有更多的現代人,卻是自願地為致富而容讓這一切發生在自己身上。只要能獲得高利潤或肥美的報酬,一切都變得可以忍受和犧牲。至於所期望的生活,等退休以後再說吧!
這種為了錢而不珍惜尊嚴和自主自由的人,正是典型的「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即使賺得了全世界,卻喪失了讓生命真正發光的寶貴機會。任何想以犧牲青壯年華的尊嚴和自由自主,來換取年老歲月時的財務自由,毋寧都是愚蠢的生命管家!
更糟糕地,如果你還經常為了致富而犧牲他人的尊嚴和自主自由,就像馬克思筆下的資本家一樣,致使那些為你工作的人淪為奴役,那麼,你就是最邪惡的壓迫和剝削者了。擁有尊嚴和自主自由,變成了一句你對部屬和員工的嘲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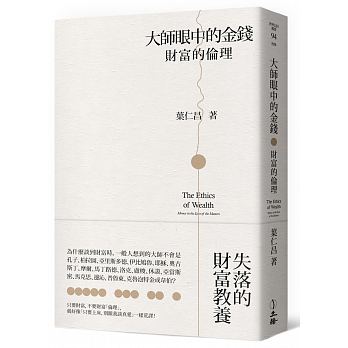
最後,對於財富的積極進取,第三個好理由是實現信仰的使命夢想,即為主賺錢。扼要來說,財富是帶著使命的祝福,並且,這個祝福是上帝為了自己的榮耀而託付於你的。
清教徒的入世聖召
最能代表此一觀點的,當然就是韋伯(M. Weber)筆下那一批十六世紀下半葉以迄十八世紀中葉的加爾文宗信徒了,尤其典型的是清教徒。在當時,他們主要是一群擁有高級技術和管理能力、並投身於工商製造業的新興布爾喬亞。
很特別地,他們積極追求財富的動機,是基於將賺錢當作「calling」的使命感,或者說,一種在世俗職業上為完成上帝召喚而承擔的責任。
他們秉持著與中世紀天主教截然不同的「入世聖召」神學,即不是否定和疏離塵世,而是加以征服和改造。借用保羅的字詞來說,他們不僅在消極上不容許社會的職業和凡俗生活淪為「罪的奴僕」,更積極地要予以擄掠和轉化,讓它們成為「義的奴僕」(羅六17~19)。
為此,他們發展了一種為了榮耀上帝,而在社會的職業和凡俗生活中,全面實踐宗教修行的「入世禁慾主義」。它首先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對工作的神聖使命感。這群新興的布爾喬亞,戰戰兢兢地投身於職場,並為此辛勤劬勞。深怕因虛擲了一寸光陰,而喪失了一寸為上帝榮耀勞動的時間(Every hour lost is lost to labour for the glory of God)。[6] 對他們來說,工作絕非只是生活的手段、為了溫飽餬口而已!它還直接關係著對上帝榮耀的見證。
其次,不只是對工作的神聖使命感,他們更在工作的性格和思維上,發展了一種特殊形式的「經濟理性主義」。一方面,他們要求工作要排除人情,並透過細緻的專業分工,來展現井然有序、循規蹈矩的理性紀律;另一方面,則要在工作中務實而理性地追求最大效益,為的是「盡其所能地」以最大成效來榮耀上帝。[7]
賺五千的勤奮管家
他們最津津樂道的,莫過於耶穌所說的那位領五千銀子又賺了五千的管家了。因為這明顯地即是以最大成效來為主賺錢。這位僕人沒有為自己留下一分錢,所追求的只是忠心而已!相反地,那位領一千銀子的僕人,將錢埋在地裡,顯然沒有任何財富動機。他只想保住那一點點錢,即使僅僅去賺利息都擔心風險。
在這個比喻裡,清教徒體會了所謂財富管家的真諦!即藉由經濟理性主義,盡其所能地以最大成效來榮耀上帝;其中沒有絲毫為己賺錢的動機和存心,只有良善和為主的忠心。而既然所賺取的一切都是為了上帝的榮耀,清教徒在花用上,當然也抱持著最大程度的節儉美德。這並非出於吝嗇守財,而是為了積累更多的資本再投入事業,來進一步創造新的利潤。
韋伯不誇張地描繪,上述的一切宗教修行,使得他們成為了與世俗繁華隔絕、拙於享受生活樂趣,但勤奮工作,又擁抱理性紀律、追求最大效益的典型「經濟人」;甚至是「一部獲利的機器」。[8]
這群人完全承認,財富和利潤心經常在「創造惡」。然而,上帝卻給了其兒女一項帶著墮落誘惑的考驗,就是要勝過並轉化它們為「追求善」的力量;[9] 即從一種對美德和靈性的障礙,轉變成對上帝旨意的積極實踐。
這絕對是個巨大改變!財富和利潤心不再等同於罪惡了,其本質毋寧是一種考驗。當然,失敗的信徒比比皆是,但這群清教徒卻堅拒一種退卻畏縮的失敗主義,並且還篤定相信,屬於上帝的選民在恩寵下的最後必然勝利。
歸結而言,對於財富的積極進取,清教徒帶給我們的第三個好理由,是實現信仰的使命夢想,即為主賺錢。一方面,財富是上帝給勤奮禁慾者的祝福。不要以為你享有上帝兒女的特權,如果你既不勤奮又不禁慾,財富是不會因為你熱切祈求或大聲宣告就給你的!另一方面,別忘了,此一祝福是帶有使命的,並且是上帝為自己的榮耀而託付於你的。而這就是你在追求致富時所當有的動機和存心,也是你花用錢財時該指向的絕對原則。
對於其中最核心的精神,十八世紀的約翰‧衛斯理(J. Wesley)歸納得好,就是「gai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and give all you can」。後來,很經典地,這三句話也成為了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終身奉行的座右銘。
成功神學的隱憂
寫到這裡,許多讀者可能會質疑,這一套財富倫理是否為成功神學的另類版本呢?或者是靈恩派的魏格納(C. P. Wagner)那種說要「破除貧窮的靈」、來實現「財富大移轉」的類似論調?
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雖然它們都肯定了財富乃上帝的祝福,並且對於致富也都抱以積極進取的態度。但一來,成功神學和魏格納丟掉了清教徒所最堅持的勤奮禁慾,改而強調你只要在靈裡充滿信心和大聲宣告,上帝就會動工,賜下成功、富裕,因為那是上帝對祂兒女的應許。
難怪!成功神學和魏格納都忽略了一種為入世聖召而禁慾的工作觀,也就是將在職場中的辛勤劬勞與榮耀上帝結合。同時,成功神學的牧師們竟然一個比一個更奢華享受。
二來,成功神學雖然也強調慷慨奉獻、為主賺錢,但那經常只是包裝!從其牧師們的奢華享受已經全然洩底了。這班人其實在動機和存心上,很大的成分是為己賺錢。上帝的角色經常淪為了只是追求財富的工具。
或許筆者可以打個比喻來作對照。成功神學是晚上睡覺時夢到自己過著富裕的好日子,然後早上起床禱告,告訴自己靈裡要有信心,上帝會祝福祂的兒女。清教徒則是晚上睡覺時夢到主禱文:「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然後早上起床禱告,告訴自己要努力工作,還要盡量節省、為上帝的國多奉獻。
十七世紀標準的清教徒,從不會因自己的富裕而高興得意,讓他們喜樂的,是自己能成為一個榮耀上帝的財富好管家。成功神學呢?讓他們高興得意的,是上帝賜下了成功和富裕。
不過,針對成功神學的此一問題,筆者要講句公道話。清教徒的那一套財富倫理,發展到了十九世紀,同樣在強大的財富誘惑下逐漸發生動搖。追求上帝國的熱情,「開始逐漸轉變為冷靜的經濟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讓位於世俗的功利主義。」最後,竟還淪為了一種在獲取金錢上「善得虛偽的良知」。[10]
這充分反映了人在面對巨大財富時的軟弱、善於自欺和虛偽的罪性。基督徒若抱持著為主賺錢的雄心,絕對可取,但務必要在靈裡面儆醒!
末了,筆者要強調,基於上述的三個好理由,追求財富固然可以正面看待,但千萬別像魏格納那樣,將貧窮或匱乏當作一種咒詛!當你綜覽整部財富倫理的歷史,可以輕易體會,貧窮或匱乏也有其屬靈價值和上帝的美意。倘若你沒有什麼財富,或在許多方面匱乏,何嘗不也可以正面看待?至於這方面的細節,在此就沒有篇幅多說了。
附註
1. 葉仁昌,《大師眼中的金錢:財富的倫理》(台北:立緒,2018),頁250。
2. 同上註,頁264。
3. 同註1,頁260。
4. 同註1,頁152-154。
5. 同註1,頁450。
6. 同註1,頁304。
7. 同註1,頁289-309。
8. 同註1,頁310-311。
9. 同註1,頁315。
10. 同註1,頁320-321。
葉仁昌

當期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