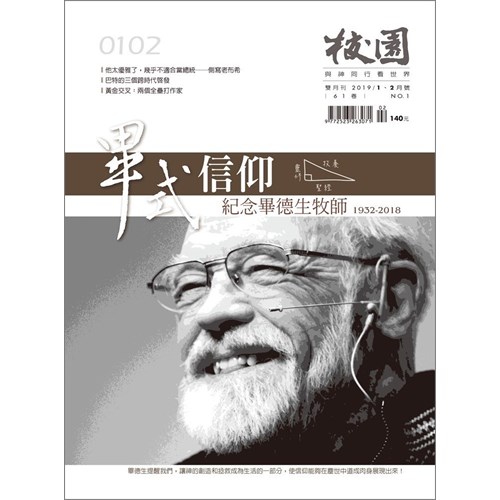
每本售價:140元

一個巴特,各自解讀;不管愛他、恨他,或有意識地忽略他,巴特仍是二十世紀神學界無可迴避的巨人。對神學圈內人來說,他是橫亙在研討會房間中的白色大象;對廣大的圈外世界來說,巴特是「福音神學」[1] 無法被現代性馴服的明據。
閱讀巴特卻不閱讀他的生命、時代,及他在當代引發的學潮,一定會失之天真;筆者只能精簡扼要地從以上三點分別梳理,巴特神學對我個人最關鍵的啟發:「巴特的務本」、「上帝的自由」,以及「基督中心的神學思考」。
資訊爆炸的當代社會,不斷索要我們的關注、參與及回應,網路使人分心。「基督徒要一手聖經, 一手報紙」是巴特的名言,意味著闡釋聖經和辦報都是很重要的工作,但巴特並沒有瘋狂到以神學人之姿投入辦報,而是回歸註釋聖經、寫作神學、牧養教會的本業。對巴特而言,「神」的問題是一切問題的源頭及答案。這是世界觀的務本。
自三十而立,巴特就確定了他的人生寫作的大方向。《教會教義學》是一項計畫涵蓋五大冊、寫作時程超過三十年的曠世鉅作。他著述神學的專注力和恢弘,別說跟當代年輕信徒比較;連專職於學術界的神學家中也再難複製。這是個人生涯規畫的務本。
一八八六年出生的巴特,著作生涯從一九一九年的《羅馬書釋義》開始。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讓他意識到整套自由神學無法作光作鹽的無根。儘管他並非聖經無誤論的捍衛者,但不論是《羅馬書釋義》、《以弗所書註釋》,以及《歌亭根教義學》、《教會教義學》都以「上帝啟示之道」作為關鍵的起頭。「耶穌愛我我知道,因有聖經告訴我。」晚年巴特訪美時的答客問,一句話總結了他神學思想的初衷。這是方法論的務本。
巴特的時代感是強的,但歷史感更是恢弘。在巴特原版的《教會教義學》中,充滿著各式各樣法文、拉丁文、希臘文的引述,而保羅、奧古斯丁、安瑟倫、加爾文、路德、杜斯陀也夫斯基、祈克果、康德、士萊馬赫等跨時代的巨人,都是他鎖定的重要對話夥伴。他感受到時代巨大的「危機」,但並沒有被發報章、寫臉書、蹭熱點、刷熱度的「需求」給佔據議程,他對歷史大問題—啟示、創造、恩典—進行深刻探究的務本精神,使他的作品仍能跨時代給予我們高度啟發。
在自由神學的傳統中,巴特早期最重視的主題可說是「上帝的全然自由」。早一批赴美求學、間接帶回巴特思想的華人神學教育者,多半吸收到的就是這個包括在《羅馬書釋義》和《教會教義學》第一冊早期巴特的主題:「讓上帝成為上帝(Let God be God)!」
讓上帝成為上帝,但上帝怎麼可能不是、或不成為上帝呢?原因就在於那個時代中,不論是自由主義、理性主義、實證主義、自然主義、歷史主義、聖經字句主義,全部都在用「自以為」的想法挾持上帝。他在《羅馬書釋義》中描繪的上帝是如此之高,高到無法親近、無法對話,原因是他認為唯有重新肯定上帝本質超越一切物質和人類想法的「不可言說性」、祂與一切受造物和人為想法的異質化,神學才能夠重新有一個「乾淨」的開始。這個開始,就是一個「全然自由、獨行其是」的神,願意將自己彰顯啟示給人。
巴特反對自由神學,因為自由神學是以人自由的想法限縮了上帝的可能。人造神可以方便地拿來為某些經濟政策優位論、人種優位論,或性別優位論背書。但巴特想要真正的「自由神」學。華人牧者的訓練背景,可說在思想上未曾經歷過巴特的「破」;無論是堂會增長的思想、門訓、愛家、讀經、求神蹟、合一等的思考,或基於社會需求的實用考量,或基於宗派傳統的因循,或基於一時一地「超自然」的領受,有意無意就將神的國度窄化了,失去了對上帝的超越性的信仰。
巴特神學被稱作「危機神學」,在於他診斷納粹時代最大的「危機」,並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神學性的—「自由神學」和「自然神學」養出的一整代德國基督教社會,居然失去了鑑別和防腐的能力,甚至支持一個將自我「絕對化」的(納粹)政府,以及它在自我絕對化後其他的強制行為。
簡單說,巴特一早就看到納粹悲劇的根源,出自「政府成為教會(自我神化)」以及「教會成為政府(自我「政治意識形態化」)」的雙重界域混淆;不論是左翼的新派自由神學、右翼偏重創造論的自然神學,都讓基督信仰不再是光和鹽,隨人間歷史糾結在必朽壞的宇宙悲劇中。
《教會教義學》第二冊談上帝的雙重「揀選」,我們必須理解到巴特所說的「揀選」不是挑選,而是指上帝「發起了特定行動」(decree)—上帝從亙古的自由/自在中啟動(proceed)了祂特殊的意志。在上帝向世界彰顯的意志中,是祂的愛、祂無保留地全然給予、祂的捨與祂的恩典。巴特直言,在上帝永恆本體(immanent)和經世(economic)的三位一體裡,我們必須聚焦在三位一體中的「子」,來掌握這個「從自由到揀選」的神聖啟示。這就是他的基督中心論。
巴特神學表述的基督,是永恆的基督,但更是歷史的基督,因祂降世為人、佈道施惠、捨己贖世,「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約壹一1)。《教會教義學》在四冊之一進入了巴特神學的高峰—被譽為心力只夠讀一冊的人必讀的「小教會教義學(mini CD)」。
巴特當然不是第一個基督中心論提出者,但在《教會教義學》五冊「啟示、揀選、創造、復和、終末」的系統進展中,基督論得以被包裹在一個極為厚實的「同心圓」中心。在「世俗現代性」拒絕特殊啟示、拒絕超越性的前設下,巴特神學自然是跟他們隔了一道無法對話的高牆。但隨著二戰、後殖民運動、後現代思潮興起,這道現代性築起的高牆被拆毀,巴特神學的爆發力匯入了被稱為「後自由神學」的繼起力量中,在近年被延伸來跟伊斯蘭、佛教、世俗主義、猶太神學、科學進行比較對話。
在近代的教會工作者中,標榜實務、立竿見影的「外功」總是較受矚目,「成功」、「效益」、「迎合(relevant & engaging)」成了揮之不去的關鍵字。巴特的《教會教義學》則提醒我們「三十年磨一劍」的務本,有其不可磨滅之悠遠價值;專注,才能深刻。彷如打地基的「內功」,才是進境高深的關鍵。
其次,我們需要重新了解「上帝的自由」。自然秩序正在被改變和超越;過往改教家在提出「兩個國度」並且從自然律思考界域範疇時,未設想到「自然範疇」會被胚胎複製人、高階人工智慧、天網、量子物理……這些科技所顛覆重劃。因此,正統教會過去的創造神學思想,除了提出節制與限制的保守聲音外,無法真正寬宏地給予屬靈資源,去滋育、祝福和牧養這些前端科技探索及應用。
但後自由神學在終末基督「更大的善與信實」眼光中,並不會僅只恐懼自然秩序被反轉或改造:「水變酒」、「復活」本身就是反轉自然秩序之事件,意味著更新的、更大的事(約十四12)將在聖靈同在的日子裡持續發生,需要以「新皮袋」去裝載。新科技將使世界進入更高速揮發的不穩定性(volatility),本身亦具有終末論的積極意義。[2]
最終,在巴特神學的「基督中心」下,「教會與世界」的關係並非純粹地對抗或殊異,而是分「內/外圈」圍繞著基督的「同心圓」關係(儘管世界並無此「圍繞基督」的意識)。這代表「外圈的公共神學」其實是一種走出圈外跟世界「搭訕」的聊天方式。在傳統「兩個國度」思想中,基督教公共神學無可避免地會傾向在世俗中尋找教會界的政治代理人(無論是邀候選人讓牧師們「按手」;或挾會眾的選票,功利地誘使政治人物口吐金句、赴聚會)。巴特神學闡明了上帝沒有「兩種心意」:一個對世界、一個對教會(如「雙重預定論」是一例);上帝只有一種(在基督裡)的心意:使宇宙萬物和好並連於祂—透過教會。公共神學只有一種議程(因時制宜用不同語言表達):宣揚上帝國度心意的議程。
當後現代社會嘗試否認「普遍性」,只提倡多中心、權宜的、肉身場域的「小特殊啟示(敘事)」時,「基督中心」能夠幫助我們「好好聊天」;聊天的目的不是為要把人摁到浸池裡,而是以「關係」和輻散的生命見證,讓世界認識位於教會和宇宙歷史的中心、受我們敬拜頌讚的那一位恩典之主!
附註
1. 此處所言的「福音神學」趨近德語Evangelisch以及歷史學者貝賓頓(David W. Bebbington)「四邊形」定義的廣義範疇,並非狹義地指美國教會文化中的福音派而言。
2. 科技在它對古典人性的「創造性破壞」中,亦積極帶領文明進一步靠向上帝所應許的終末—並非憑它自己的能力,乃是那叫它如此的。當世界邁向它在有限時空中存在的目的(telos),教會反而不該因無知、懶散和保守「絆住」 了文明前進的腳步,以致在終末被主審判是個「又惡又懶的僕人」!
當期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