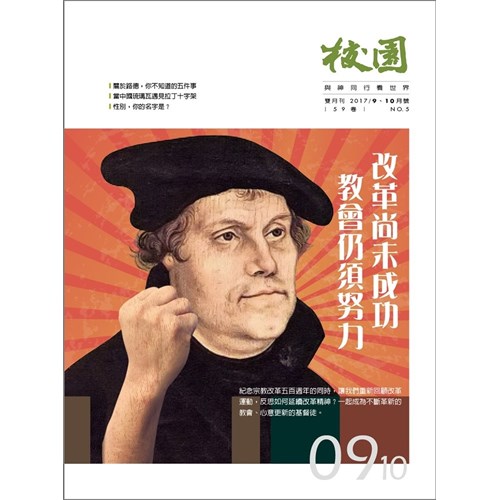
每本售價:140元

當我像曦子十三四歲這麼大的時候,暗地裡不只一次想要做個男孩。
並不是我對女兒身有什麼意見,也不是爸媽在教養上重男輕女,而是那些壓抑在心底的不滿冒了出來—從家庭、學校到社會,對女生的諸般要求甚至限制的不滿—「女孩子家不可以像野馬,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女同學們時時要莊重!」「天黑以前要回到家,不可以自己一個人搭計程車,知道嗎?」童話裡的公主需具備同個模子刻出來的美貌與美德,才能得到王子的青睞、百姓的肯定;現實中,我和同學也被期待穿上花色雷同的乖乖女衣裳,不管合身不合身!而豆蔻年華,穿過大街小巷,總得時時提防角落的暗影與耳語。相較之下,男生頭上的天、腳下的路好像都寬闊許多。
兩年前,曦子剛上初中,幾次要求自己單獨走路上下學,當我們出於安全考量拒絕時,她的回應令我耳熟:「為什麼哥哥可以我不可以?為什麼同學可以我不可以?」那時我讓另一半解釋,選擇不透露自己曾經的心事。
春花四月,動漫影史上全球票房冠軍,日本導演新海誠的《你的名字》,熱火延燒半個地球後終於來到北美上映。不敵兩個孩子殷殷期盼之情,我破例上網買了預售票,早早就和他們一起坐進電影院裡。開演不久,一個場景深深扎入我心:十七歲女主角三葉,無可奈何地表演完神社祭奠儀式後,走下長長石階時向遠方忘情呼喊:「我討厭這座小鎮!我討厭這種人生!下輩子請讓我成為東京的帥哥!」這樣的吶喊,無盡地迴盪在曦子(以及當年的我)的心谷裡。
三葉,一個成長在偏僻山村,繼承家族神社代代相傳習俗的少女,她的掙扎,象徵著這一代日本少女在傳統與現代、鄉村與都市、男性與女性……意識變換洪流裡的掙扎。
當三葉「夢見」自己變成高中男生,當東京少年瀧「夢見」自己變成深山裡的高中女生,當他們發現夢境其實不可思議地流入真實,藉著三葉和瀧奇異的靈魂互換,推進的不僅是故事情節,也直逼兩性互動裡一些基本問題:
Q1. 兩性對彼此身體╱生理的理解與聯結,也同時代表心靈方面的理解與聯結嗎?
Q2. 三葉最後還是心甘情願地扮演女性角色,這是成長成熟的過程,還是無奈地接受現實?
Q3. 「你的名字?」「你的名字是?」電影裡關於名字的提問貫穿整個故事。名字,是人們最根本的身分指標與認同,問名與尋名在藝術與心理學上有深層的象徵意義—在尋尋覓覓的過程間,關於身分的其他問號也會鋪天蓋地而來……包括性別。
青少年時期摸索性別典範,摸索自身性向的課題不是當今才出現,然而今日與昔日現實的性別情境確有差異。當我像典兒、曦子這般年紀時,關於性別,只有男女兩個選項;現實裡我的掙扎,在於搞清楚,決定要不要活出社會對女性的規範和期待。典兒與曦子依然面對男女兩個大寫選項,不同的是,旁邊多了幾個印痕淺薄,但已經可以辨認的其它選項:同性、中性、雙性、無性……。多年前有些少年的無聲吶喊,偷偷摸摸的耳語,暗地糾結的疑慮,如今似乎都可以在檯面上理直氣壯大聲討論,也可以在傳播媒體上看到以往少見的各種非傳統形象。
典兒高一、曦子初二 (可見年齡層越來越低)時,都曾頭一回提到同學表白自己同性、雙性、變性的心志。這個暑假正在修社會學概論的典兒解釋,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性別有生理性徵、性別表達、性別認同三個面向,而後二者相當程度上是社會化的過程。換句話說,多元化社會也會允許多元化的性別表述。
可以公開討論不是壞事,但性別多元的另一面有可能是雜亂混沌的景象。社會轉型、眾聲紛紜時,孩子要尋找清楚的性別定位區間,變成越來越模糊;雖然青春小鳥向來難以關在一言堂的籠子裡,但我,也不願他倆在眾聲喧譁裡越來越聽不清真音。當性別在世人中漸漸成為一個流動多元的概念,我該怎麼和孩子對話?(不能再像兩年前那樣一路沉默著了)

想起一位深愛的奇幻文學作家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她的父親是柏克萊加州大學文化人類學先驅,母親是心理學家,家學淵源,勒瑰恩的思想深受人類學民族志、榮格心理學影響。她自己也對女性主義思潮、性別理論、道家哲學(曾經花了十幾年翻譯《道德經》)有長期的深刻咀嚼。作品類型跨越奇幻、科幻、評論與詩集,流傳最廣的作品是科幻小說《黑暗的左手》和少年奇幻《地海》系列,後者常與托爾金的《魔戒》三部曲或魯益師的《納尼亞傳奇》相提並論。
《地海》系列原本是三部曲:《地海巫師》(A Wizard of Earthsea)、《地海古墓》(The Tombs of Atuan)和《地海彼岸》(The Farthest Shore),成書於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二年間,當時勒瑰恩四十歲左右。她回顧創作生涯時,自承《地海巫師》寫作的風格手法、故事的重點鋪陳,都屬男性視角,「我那時像一個傳統男性(西方白人)作家那樣寫作」—不僅因為閱讀經驗影響,也是那個時代要發表奇幻類型作品途徑受限:「如果不以那樣的方式寫,就沒有出版社接納。」
《地海巫師》帶讀者進入地海世界,認識才華橫溢、心高氣傲的少年雀鷹(真名格得),走上自我追尋的旅途。《地海古墓》裡出現了恬娜,她自幼在沙漠中古老陵墓長大,與世隔絕,命定成為歷代祭拜「累世無名者」的女祭司,直到偶遇闖入古墓、搜尋厄瑞亞拜之環(地海群島的和平象徵)的格得。恬娜迷惑了,她該謹守命定,服從祭司職責,坐看格得被囚,還是要相信他身負重責,相信黑暗陵墓外另有個遼闊天地?
《地海》三部曲落幕近二十年,從未絕版,經典地位無可動搖,勒瑰恩出人意料地又吹起地海樂章;《地海孤雛》(Tehanu)在一九九○年的出版震驚了評論界與讀者圈,它和之前的三部曲呈現渾然兩異的閱讀體驗:知命之年的勒瑰恩,以女性思維重新思索地海世界,溫柔開啟地海尋常門扉。經由垂垂老去、魔法已失的巫師格得,與隱居鄉間的寡婦恬娜重逢,加上恬娜收養的神秘孤女瑟魯,在三人表面看來平常不過的生活中,勒瑰恩探問兩性良性互動的幽微可能。書裡角色不再施展驚心動魄的魔法,也幾乎沒有上天下地的冒險,反倒細膩描述家居農活瑣事……這豈不是太平凡、太無聊了?
然而在這些柴米油鹽的煙塵裡,勒瑰恩不時呈上粗胚碗,碗裡的清水閃耀動人的波光。好比格得與恬娜的對話:
「為什麼男人怕女人?」恬娜問。
「如果你的強勢不過是對方的軟弱,你也會活在恐懼裡。」格得回答。
「沒錯;但女人似乎也害怕自己的力量,她們害怕自己。」
「有人教過她們要信任自己嗎?」格得問,這時瑟魯正好進來,他和恬娜四目相對。
「沒有,沒人教過我們信任。」恬娜回答,她看著孩子把木頭堆在箱子裡。「如果力量是信任。如果力量不是那些上下階級的區分—帝王、巫師、地主那些沒必要的區分—那麼真實的力量,真實的自由就在於信任而無關勢力。」
「就像孩子信任他們的父母。」格得說。
每一個說故事的人,都得取得讀者的信任,讀者才不會轉身離開。
勒瑰恩等待了二十年,等到自己練習好了新曲調,等到了世代允許,說了個不一樣的故事,呼應她寫作《地海古墓》時開啟的初心:「我的心堅定地提醒我,兩性缺了任何一方都走不了太遠。因此我的故事裡男性或女性少了對方就得不著自由。」
福音書裡,耶穌在世上與女性互動,無論是他的至親、跟從他的姐妹、群眾裡久病的婦人、犯罪的女子、憂慮的母親……每個場景,每句話語,細細咀嚼,常讓我深深感動。主耶穌對女性的尊重、體恤、寶愛,在當時是反主流文化的吧?今天呢?祂會不會還在等待一個個預備好聽見祂的靈魂?
對典兒與曦子來說,在成長成熟的路上,做一個「合神心意」的男子或女子,究竟意味著什麼?路程剛起頭,他們需要持續從閱讀裡、從生活裡、從與上帝和他人於自己的對話裡,琢磨出上帝造男造女的深意。這是不能逃避、無法速成的功課!
這一代的孩子何等需要清澈的引導、明淨的鐘聲,才能在時而緩慢、時而激盪的性別議題洪流裡不會載浮載沉,不會陷入河底的污泥。
我禱求在這個過程裡不缺席。
當期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