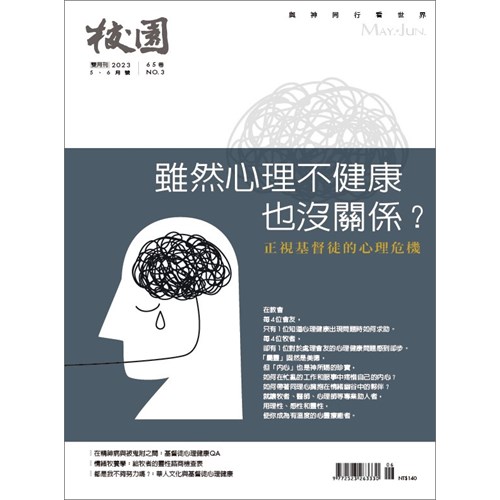

俗話說:「天助自助者,自助人恆助之。」這句俗語說明老天爺只幫助那些願意幫助自己的人。儒家也說:「人必自助,而後人助。」如果一個人願意幫助自己,其他的人也一定會來幫助他。這些俗語都表達了華人文化中,人們歌頌與看重「勤奮自助」。「努力」是華人文化重視的價值,同時也已經成為國民性格。西方研究儒家思想有名的學者墨子刻 (Metzger)[1],發現華人具有依賴、逆來順受、進取、自立、自主等特質。努力往往被視為一項美德,也是一個人應該盡的本分,更是一個人追求成就的工具,相信一個人可以透過努力來增加自己的能力和智力。周慕姿心理師所著《過度努力》一書中,提到有人會用努力把內在的傷藏得很深;有人把努力追求成就當作最完美的人生,努力追求外在成就或滿足他人期許,卻忘了自己是誰?自己為誰而活?讓我們感到好奇的是,這些表面上看似正向積極的努力,如果演變為過度努力的話,也會造成心理上的傷害,失去真實的自己。生活在華人文化圈下的台灣基督徒,是不是也帶著努力的意識型態?這樣的努力文化跟我們的信仰有衝突嗎?筆者認為除了從現象面釐清該問題,還需要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來思考,每一個文化因素和整個文化系統之間的關聯。
中國地區的先民因天命之不可知、不可信,唯有求之於人的自身,所以漸從宗教上對神明的倚賴解脫出來。[2] 於是從殷人的「敬天」到周人「修德」,人格神的觀念淡化了,天帝的觀念退居二線;只是保持其神明不測的超越性,而價值活動的中心則轉移至人的身上,注意自身有否修德。以德配天,成了打通「上『天』下『人』」,使中國古代思想自此從「神本」走向「人本」。[3] 孔子認為「為仁由己」,孟子說「人皆可為堯舜」,重點都是放在個人的內心自覺;追求價值之源是從個人內心去自我覺察,而不是向外向上、尋求上帝來「啟示」的;把注意力回歸到自身的努力上,於是開啟一股「反求諸己」的精神之風。
一開始,個人的努力是為了修養品德,後來受到科舉制度的影響,反求諸己的品德修養進一步世俗化;努力則成為追求成就目標的工具,只是為了達成社會期許作為目標,並不是為了個人興趣而努力。例如努力讀書是為了能夠進入較好的大學就讀,將來可以找到較好的工作。這樣的努力看起來是積極的人生,可是個人卻不快樂;因為一個人失去個人的真實,也不知道努力本身的價值。有些人把努力當作達成目的之工具(工具型努力),有些人努力則不在乎行為的效果,而是重視個人努力的動機、努力的行為是否符合公認的道德規範或標準(好比盡心)等,至於努力的結果就不是他們所重視的(義務型努力)。例如學生經過努力,雖然成績不理想,可是他已經努力了,父母和老師就不會去苛責。這種人但求行為符合道德,他人長期期待自己符合角色義務,如果沒有做到,內心就會感到愧疚。而所謂健康型的努力,是個人拿掉這個社會的倫理束縛,按照自然的方式,返回到一個真實的自我狀態的「自在型努力」。這時人才會進行自我反思,從外在價值走向內在真實的價值;從努力作為工具、手段,走向努力的目的是基於努力本身(end in itself)。綜合以上所介紹的三種努力類型,說明如下:

努力是否會遭遇困境呢?人可能會被責任感、理想給「套牢」,如何才能讓自我「解套」,可以自在地努力而自得其樂呢?另外,人在努力的過程中,面對無可奈何的現實環境,個人如何才能超越環境的限制呢?勞思光先生 [4] 在他的《中國哲學史》裡,曾用「義命分立」來概括儒家在命的前提下,先民所持的努力態度。命是外在於人而不受人控制的,在命的範圍內,人是不自由的,這是屬於實然範圍。但義卻是內在於人,而且是可被人主宰的;在義的範圍內,人是自由的,這是屬於應然範圍。例如我天資笨拙是一回事,我應該努力學習卻又是另一回事;天資不是我可以自由選擇的,但是努力卻是我個人可以自主決定的。孔子說:「為仁由己。」(《論語.顏淵》)孟子也同意孔子的說法,更積極地採取立命的想法,他說:「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壽命的長短是被決定的自然現象,個人不應憂心於此。相反的,個人應該超脫生死的憂慮,只要致力於能夠自作主宰的修身行義。一個人究竟要努力到什麼程度,才可以放下重擔呢?當「盡人事的努力」已經無法再有任何結果時,人只能採取「聽天命」;個人服從上天或是自己的命運,放棄安排自己的命運,配合上天的安排。儒家「盡人事聽天命」的文化設計,一切要先「盡人事」,而且要盡心付出,以求自己坦蕩無愧,然後才進入「聽天命」,如下圖說明:

中國主流哲學思想中,對「自己」非常重視,並委以重任。[5] 華人透過「修德以配天」的想法,從神本走向人本,人開始有了反求諸己的精神,彰顯了人的自主與能動性。因此,華人將個人命運的掌控權很高比例地放在個人身上,期待透過自我努力來提升自我的命運與道德高度。然而基督教的世界觀相較華人的世界觀,比較特別的是加入了「人格神」的視野,這挑戰了華人那固有的「以人為本」的道德精神。以弗所書二章8節:「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在下一節(弗二9),保羅繼續論述:「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聖經除了肯定人的得救是來自神的作為,更進一步否定人可以藉由努力的行為來拯救自己。可以說,「恩典」不只是肯定、確認有一個從上而來、外在於人的行動者,會主動施與恩惠;它更要求恩典的接受者承認自己的缺乏與不足,放棄任何自我救贖的企圖與任何足以讓人「自誇」的舉動。保羅在羅馬書七章18~19、24~25節中這樣說:
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保羅首先肯定自己確實有「行善的欲望」,因為在他心裡有善惡的良知;但是他承認自己雖然有行善的動機,卻沒有行善的能力,因此他感嘆自己「真是苦啊!」他就像是個認知失調的人,知道應該做卻做不到,知道不該做的卻反而去做了。然而,保羅有一個更深的盼望,那就是「靠著耶穌基督」。保羅承認自己全然的無助、敗壞,因而承認他只能「靠著耶穌基督」來脫離罪惡。保羅完全棄絕他那「取死的身體」,不將盼望放在自己的自我要求或道德之上;因此,他將盼望轉而放在耶穌基督身上。我們看見,對自己行善能力的絕望,是迎向恩典的第一步。如果我們本身根本就是溺水的人,毫無能力可言;這時只能用替代法,就是接受耶穌所賜的「白白恩典」,接受救生圈,才能得救。如果你長期以來努力,都是在為別人而活,反而逃避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你是誰?你為誰而活?這樣,你就需要回到以神為中心的信仰,才能找到生命的意義,因為你是神所創造的。恩典通常被視為免費饋贈的東西,恩典不是靠努力奉獻、努力服事、努力做一堆上帝喜悅的事就能獲得;恩典也不是我們透過自我修養的道德,來換取什麼好處。恩典是上帝自發性的行動,源頭是祂那完全的愛,而人只要單單相信就能得著。華人文化中缺少了一位主動愛人的神,因此人們將道德的重擔都放在自己身上。基督信仰則要求人們放棄自我救贖,承認自己永遠做不到完美,轉而去認識這位主動愛人的神;恩典是來自於外在所賦予的好處,與自我的條件完全無關。
儒家文化的努力模式一切要先「盡人事」,而且要盡心付出,以求自己坦蕩無愧,然後才進入「聽天命」。與儒家文化模式比較,基督徒在努力的優先順序上又有何不同呢?馬太福音二十二章34~40節記載法利賽人問耶穌:「夫子,律法上的誡命,哪一條是最大的呢?」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耶穌想要提醒法利賽人的是,「如果沒有祂使罪得潔淨,如果被救贖者心中沒有聖靈能力的同在,任何程度上的愛神都是不可能的。」從耶穌的回答,我們可以看出基督徒的優先順序是先愛神,其次才是愛人;一個充滿神之愛的人,不會只滿足於造福自己的家人,反而會推己及人,渴望造福全人類。基督信仰帶給我們的人生觀,是以神為中心,一切要先「聽天命」,然後才進入「盡人事」;一切自我的精進是為了榮耀神,恩典使我的努力更有價值。因為這不是外在的成就,而是關乎我的生命問題。仰望恩典不等於懶惰不盡本分,這樣的努力也不是要求自己要夠好、夠完美,而是天父對我們說「孩子我知道你做不到,讓我來陪你一起完成」。在恩典裡努力才不會白費力氣,在恩典裡的努力才會是輕省的。
附註:
1. T. A. Metzger, “Selfhood and authority in Neo-Confucian political culture,”in A. Kleinman & T. Y. Lin(林宗義) (Eds.), Normal and Abnormal Behavior in Chinese Culture (Boston: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2.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台北:學生書局,1973;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牟宗三,《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3. 余英時,《內在超越之路:新儒學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1992。
4.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卷,台北:三民書局,1984。
5. 李澤厚,〈孔子再評價〉,《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台北:谷風,1986),頁16~17。